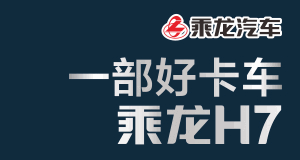昌河重組前景仍步履蹣跚:北汽最快本月接盤
對于這一說法,昌河汽車相關人士則鄭重否認了鈴木從昌河撤資的消息,表示雙方仍為合資伙伴。
真正引起長安與昌河關系破裂的導火索則緣起于去年的那場罷工事件。“長安想把我們九江基地的轎車生產資質轉移給長安馬自達,后面的事(指罷工)你也就知道了,他們沒拿走。”陳洱向記者表示。
“李黎(長安派駐、昌河汽車原總經理)走了之后,長安派來的財務總監職位還在,但也就沒來上班了。目前我們內部已經把長安的標志都給撤下來了。”蘇易告訴記者,“這些年長安在資金、車型、技術上都沒給過昌河多少支持。”
“資金方面貌似都是空的,但是在車型方面長安有向昌河的合肥基地投入過一款福運面包車,原型車是他們的。但現在脫離關系了,車也停產了。”陳洱表示。
“(長安給昌河的)支持當然有了,一直以來都有很多的支持。”在電話中,中國長安集團相關人士激動地向記者表示,當被問到能否舉例一二時,該相關人士只稱,“比如就太多了,無論哪方面都有支持。”
當記者向前述中國長安相關人士求證昌河是否已脫離長安時,該人士表示昌河鬧獨立一事進行已久,“也沒必要隱瞞什么,但‘昌河脫離長安’這個說法并不是很準,現在來講,還不是完全脫離。或者說是叫重組,相當于股權關系的劃轉,昌河由原來的中央企業劃歸到地方。”
而當被問到對于重組昌河的這幾年有何評價時,前述人士生硬回答“沒有評價”。
對于昌河獨立后的基地分配,如同此前媒體報道一樣,幾名昌河員工均向記者證實合肥基地將作為補償的“分手費”無償留給長安,但此前合肥基地生產的車型將全部拿回江西。
“合肥基地生產的是我們的自主品牌,包括商用車。目前還處于遷線狀態,所以我們十月份是沒有生產商用車的。”蘇易告訴記者。
“現在正在遷線,把三排貨車這塊生產業務遷到九江去,面包車這塊則遷到景德鎮去,這個工作可能到年底結束。”陳洱亦證實了以上說法。
而關于合肥基地的生產資質,陳洱及蘇易告訴記者,合肥基地是昌河汽車的生產資質,只能生產面包車與貨車,“昌河汽車與昌河鈴木的生產資質都在昌河自己手上,長安也不需要這一塊。”
對此,中國長安前述人士則持不同意見,“合肥基地本來就是長安的,生產資質也是我們中國長安的。”
而據記者從網上資料了解到,合肥昌河前身是原安徽省淮海機械廠,1997年昌飛將其并購成立合肥昌河汽車有限責任公司。1999年,實施股份制改革后,合肥昌河又成為昌河汽車的合肥分公司。2007年合肥分公司又變更為昌河汽車的全資子公司,被中航定位為昌河汽車自主品牌產品的生產基地。
或借重組迎來春天
與長安的“包辦聯姻”以“分手”告終,好不容易單飛成功的昌河,下一步該怎么走,堅持獨立還是繼續找個好人家接盤?所有人都在觀望。而以目前昌河的處境來看,重組似乎更有前景。
“在談的有好幾家,北汽、一汽、江鈴據說都有來和昌河談過重組,中通也有人提過,但是應該可能性不大。”陳洱告訴記者。
蘇易則向記者表示:“聽說省政府比較希望我們跟江鈴重組,但是江鈴里有長安的股份,比較復雜。如果不出意外的話我們猜測是跟北汽重組。”
北汽似乎是眾望所歸。今年6月,北汽集團董事長徐和誼曾表示,今年內至少會兼并重組一家車企,如果順利,年底前兼并兩家整車國有企業。有媒體爆料稱在不久前北汽集團的一次內部會議上,徐和誼提及北汽未來還將有個江西基地,昌河呼之欲出。
“這個消息目前我也不清楚,還在了解中。”與昌河官方態度類似,記者向北汽集團公關部人士求證時,對方回答的也相當謹慎。
相較于對長安的抵觸情緒,提及未來可能與北汽的合作時,幾名采訪對象明顯頗為看好。“北汽的兩個副總都是以前在昌河的老總,可能會給我們一定的支持。”蘇易表示。
“如果要跟北汽重組的話,發展前景會好些。北汽自主品牌這塊,有威旺、北汽汽車、紳寶,它的弱項是網絡這塊,我們從80年代開始做微車,2000年開始做轎車,這方面應該是我們的強項。如果跟北汽在車型和資金等方面實現深度合作,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只是表面上靠管理的話,前景還是比較好的。”陳洱則看得更遠。
在車間工作的楊山則向記者透露,北汽已經把車型都給了昌河,可能下個月便會簽約。“現在昌河有條新的生產線,本來是為了生產從合肥拉回來的福瑞達,未來應該也會生產北汽的車型。”
對于近年來積極擴張布局的北汽來說,擁有景德鎮、九江兩個基地30萬整車產能、15萬發動機產能的昌河汽車,在微車領域的經驗豐富,又手握昌河鈴木轎車生產資質和鈴木車型,這不啻是個好選擇。身為四小汽車集團之首的北汽長期“坐五望四”,超越第四長安已經箭在弦上。
但與此同時,要接手這塊“燙手的山芋”,北汽所需承擔的顯然并不輕松。如果重組成功,北汽身上肩負的還有幾千名昌河員工的期望,而不只是個冷冰冰的基地這么簡單。
自2009年國家發布《汽車產業調整振興規劃細則》指出,擬通過兼并重組,形成2家至3家產銷規模超過200萬輛的大型企業集團后,一股兼并重組潮席卷而來,小車企們或持生產資質待價而沽,或垂死掙扎奮力一搏。從輝煌到沒落,從“指婚”到再“擇婿”,昌河的故事或許有其特殊性,卻也折射出在這一波浪潮下小車企們的遭遇和故事。
那么,昌河的春天有多遠?
“昌河這么多年了,我們家也一直都是昌河員工,看著它從開始的微車老大到現在的份額萎縮,也很無奈。跟誰合并重組并不重要,只要員工的待遇提高了,跟誰都沒意見。”楊山無奈地說道,隨即陷入沉默。